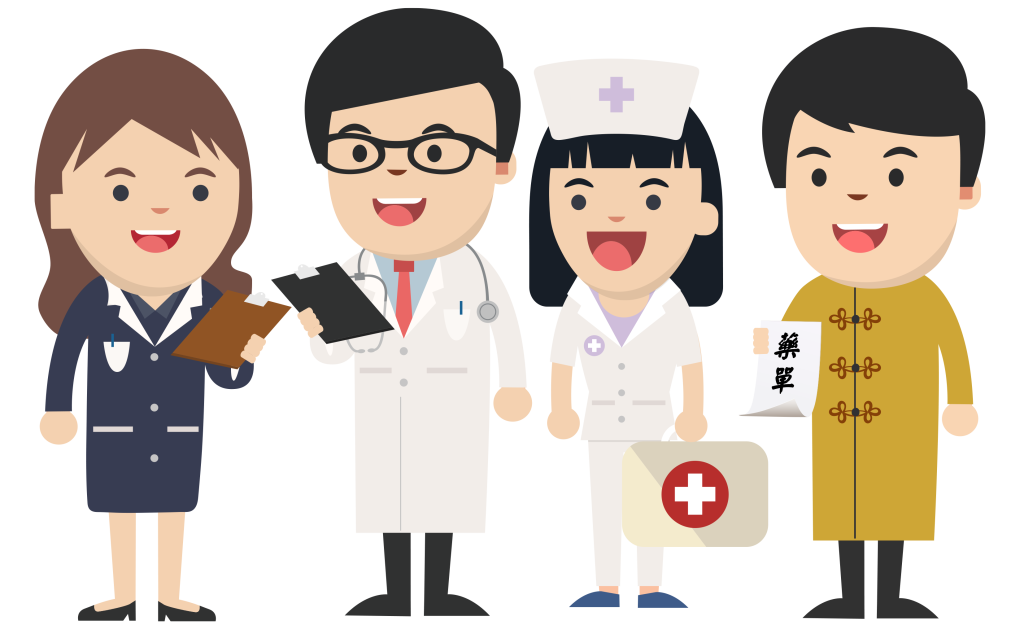【不綁老人.四】香港首間「減綁」安老院院長:人手非最大困難
不用再「綁人」的保健員影梅,還有不再需要「被綁」的發枝伯伯,都是來自薄扶林一間政府資助院舍「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」。這間背山面海的單幢四層高樓房,環境清幽,只是此前的許多年,它都算不上是院友的「五星級的家」,皆因院內逾半老人長期被綁,不少更是患上腦退化症(又稱認知障礙症)的老人家。
直至2016年,有一點「火種」落到院舍年輕院長梁曙㬢的心頭,改變了這些被綁老人的命運。「有一年,我參加了耆智園的課程,有關如何照顧腦退化的長者。課程講到,綁還是不綁老人好?」
攝影:高仲明
(不綁老人系列專題七之四)
整個團隊不斷想,如何為長者行前少少,擺脫舊有觀念。
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院長 梁曙㬢
推行不綁老人計劃的年輕安老院院長梁曙㬢,本身是社工出身,他記得當年參加一個有關認知障礙症長者的課程時,課堂上有講者說,老人在院舍是三等公民:等食、等瞓、等死。「這一句對我們來說,好hurt。做院舍,我們不是想老人家在這裡『安老』嗎?」
「好坦白講,我們以前的服務,好似與『安老』這個字有點違背。」梁曙㬢有深刻的反思:「我們的團隊不斷想,如何為長者多想一些、行前少少,擺脫舊有觀念。」於是,他重新檢視「約束」老人這回事,也在院舍破格推動「不綁老人」。
投訴文化讓院舍卻步
「綁,其實浪費人力物力,老人家亦不會開心。」所謂綁,老人會被穿上安全衣、帶手拍(即手套);員工綁人時,老人掙扎一陣子,他們又要蹲在床下打幾個結,擾攘一輪,起碼需要5-10分鐘。以往一間房5個長者3個要綁,一間院舍,為了綁人而耗費的人力物力,有數得計。
梁曙㬢心忖:「有沒有其他方案可以雙贏?同事不用做那麼多,老人又開心?」他帶著這種想法與院舍的主管研究,大家都認同推行減少約束。只是,要擺脫舊有觀念與習慣,知易行難。院舍的營運者,何嘗不是被「約束」?「現在NGO(社福機構)問責文化、投訴文化好盛行,做錯少少都會面對投訴,弄得好多主管都好怕。如此,還夠不夠膽試新?還是做回以前的事?」
部署半年
然而,他們還是選擇了為院舍老人,冒一個險。要推動減綁政策,做的不僅是鬆開那個繩結那樣簡單,而是將院舍照顧老人的老舊問題「連根拔起」地改革。他們意識到,過程要由上而下(top-down)、也要由下而上(bottom-up)才會成功,不是管理層一聲下令「不綁」便能成事。所以在推行前,他們花了半年時間部署。
其實,老人晚上「擒床」,與深宵時睡醒有關。一般院舍作息時間要遷就員工交更,出現了老人院常見、違反生理時鐘的作息時間表:下午4、5點「晚飯」、晚上8時就寢。為了配合減綁政策,院舍重整員工每更工作時間,或縮減或延遲,讓老人回到6、7點晚飯、9時許入睡的作息規律。老人入夜後安睡,最終是減少了深宵睡醒後「擒床」問題,紓緩了通宵時份的照顧需要。
然後是跌倒。歸根究柢,身體無力是跌倒主因之一,這與缺乏運動甚至營養有關。院舍於是加強物理治療、活動等配套,讓老人家盡量維持肌力。院內曾有老人由不良於行,練習至可重新用拐杖走路。院舍的餐單亦由只顧營養輕視口味,改良至有「老人院版」的燉蛋和西多士等,餐單設計的邏輯是老人愛吃才有營養、才有力氣。梁曙㬢說,院舍現時每月200多萬的營運成本中,約8-9%都用於膳食。
讓照顧回歸人性
「不是要求同事一開始便全部不綁,如此會好大風險。我們逐個個案去試,每個月減少一些。」和他一起討論的,包括護士、社工、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以至前線保健員等。團隊最終在2017年初,選定了首批試行個案,都是經評估後認為較大機會「減綁」成功的長者。
「可能因為被綁,老人要掙扎才會擒;但又因為『擒床』這行為,令他們被年復年被綁。」他記得有個叫阿冰的婆婆,因插喉而被綁手多年,「不綁之後,她沒有拔過喉,一次都沒有。」梁曙㬢回頭再看:「也許早在三、四年前,她已經不需要被綁了。只是沒有人review(重新評估)她的情況,白白被綁多年。」
據他們統計,院舍由高峰期逾半老人被約束,減少到現在只10%左右;上月共26人需要使用約束品,其中七成以上只在需要時(如晚上)才使用。而推行減少約束計劃後,院友跌倒個案反而有顯著下降的趨勢,2016年為80人、2017年為35人,2018年(截至5月)為13人。
梁曙㬢坦言,推行不綁措施一年半以來,約60多個減綁個案中有20宗失敗,約佔三分之一,原因都與無法解決當初被約束的原因有關,如依然拔喉或抓損皮膚等。但其後,這些老人即使復綁,程度也會減輕或時間縮短,例如由本來綁在床上減至坐高背椅等。「失敗不要緊,起碼我們加深了解,下次再試時便可考慮其他方法。」他說。
人手非最大因素
自從年前大膽試行不綁新政,他們的經驗成為本地安老院舍業界的先例,時有同業來交流取經,差不多每一次都有人提問:哪有人手?人手比例要幾高才做得到?行內都知道這間院舍一直以較優厚的薪酬聘用人手,難免將不綁與人手比例,想像成有必然的因果關係。
梁曙㬢說,院舍沒有為不綁而額外聘用人手,一直維持原有的人手比例去執行。但因考慮不綁老人的文化需要團隊認同,故近年停止聘用「外購人手」(即行內的自由工作者)擔當前線照顧工作。
梁曙㬢理解業內人士對人手調配的顧慮:「只是因為他們沒有試過。他們會覺得,不綁便要額外人手『睇實』這些個案。這只是第一步要做的事,長遠並不會這樣。反而在鬆綁後,院友狀況有改善,可照顧自己,往後便不再需要找人緊盯著他們。」
「在我們的經驗裡,不綁,人手並非影響成效的最大因素。最重要是同事是否懂得處理這些個案?有沒有人幫他們過渡(不綁的工作模式)?這是技巧、知識和價值的層面。」
長遠而言,不綁才更有效調配人手:「香港的思維是院友一定在老人院終老,是create dependence(製造依賴),沒有想過去維持或提升老人的能力。」若改變傳統觀念,職員的時間與心思用於改善服務配套與質素,如搞活動、關顧老人,而非綁人防跌,照顧的工作便比「綁人」更有意義和價值。
要求不被約束並非奢侈品
由新丁走到今天,梁曙㬢看著老人服務的變遷。「我在這行十多年,每年代都有不同要求。以往會講讓老人有食宿;十年前講有沒有活動;五至七年前講護理質素;兩、三年前講虐老。近一、兩年開始講人權、自由、長者自決權。」他認為,在關注老人權益的年代,不在臨老、臨死時被綁,已被視為所有人應份擁有的權利。「要求在院舍食魚趐是奢侈品,社會價值觀未必認同;但這(不綁)不是奢侈品。社會人士都會認同,只是擔心是否做得到。」
其實早在2006年,本地已有團體研究約束問題,但十多年來,業界沒甚反響,老人仍得靠每天「金蟬脫殼」來對抗被綁。環顧亞洲區,日本厚生勞動省早於1999年已頒布省令,一切與老人照護(介護)、看護有關的活動,無論是設施還是居家,除保護生命的緊急狀況以外,所有情況禁止拘束老人。相比起來,香港步伐很慢。
但如今,梁曙㬢卻見到轉變的契機:「我想業界已預備迎接這種轉變。」現在,這間院舍在長者入住時,不會立即要求家屬簽定約束同意書;前線職員交更時,亦不會第一時間想為哪個老人用安全衣。取而代之的,是真真正正有關照顧的討論:不如早上試試不讓某個老人睡很多?可否給某老人設計活動?這樣做他的情緒會平伏一點嗎?
要做到這種地步,才是「照顧」質素的真正質變。
原文:
https://www.hk01.com/%E7%A4%BE%E5%8D%80%E5%B0%88%E9%A1%8C/201855/%E4%B8%8D%E7%B6%81%E8%80%81%E4%BA%BA-%E5%9B%9B-%E9%A6%99%E6%B8%AF%E9%A6%96%E9%96%93-%E6%B8%9B%E7%B6%81-%E5%AE%89%E8%80%81%E9%99%A2%E9%99%A2%E9%95%B7-%E4%BA%BA%E6%89%8B%E9%9D%9E%E6%9C%80%E5%A4%A7%E5%9B%B0%E9%9B%A3
「宅醫學堂」學習更多知識→
更多「老友新聞」→